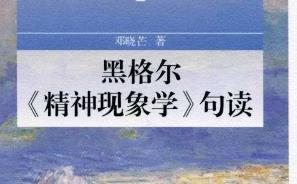最近兩、三百年來,德意志民族的哲學天才所放射的光輝是無可比擬的,這個民族理所當然地在哲學領域中占據著第一把交椅。于現代人來說,不懂德國古典哲學,就不懂得如何作真正的哲學思考,也無法把握現代哲學思想的來龍去脈。
那么,德國古典哲學是如何產生、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呢?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德國資本主義也開始有了緩慢的發(fā)展。由于在經濟上有英國工業(yè)革命的推動,在政治上有法國革命的影響,德國資產階級也有了改變整個封建秩序的要求。但與此同時,法國革命玉石俱焚的后果也使德國資產階級膽戰(zhàn)心驚,使他們的行動更加小心謹慎,對自己的前途更為動搖和猶疑,另一方面,也迫使他們回到內心去對人性和社會作更加深入徹底的思考。德國古典哲學就是這種時代精神和社會思潮的反映。
當然,一種哲學思想除了受到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影響之外,還取決于它從傳統(tǒng)的思想源流和外來的流行思潮所接受的影響。在傳統(tǒng)方面,德國人比英國人和法國人在某種意義上要更加得天獨厚。德國傳統(tǒng)的思辨精神是從萊布尼茨—沃爾夫派的哲學中形成起來的,但最早還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庫薩的尼古拉。十八世紀末的德國啟蒙運動涌現了一大批像萊辛、溫克爾曼、鮑姆加通、赫爾德、歌德、席勒這樣的啟蒙思想家,催生了“狂飚突進”及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的一個接一個的社會文藝思潮,使得德國人在歐洲思想舞臺上充當著越來越積極的角色。德國古典哲學是在哲學已經相當程度上擺脫了神學的束縛,哲學與社會思潮和時代精神的關系日益緊密,哲學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已經被理性派和經驗派哲學明確提到了哲學研究的日程上來的前提下,開始自己的行程的。我們讀德國古典哲學的原著會有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自從康德以后,哲學開始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思想更為復雜,句子更加難懂,行文和專業(yè)用語底下包含著大量的潛臺詞,未經過專門的哲學訓練幾乎就如同讀“天書”。哲學不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問津的學問,而成了大學教授的專業(yè);不再是單憑業(yè)余自學(如笛卡爾、斯賓諾莎等人)可以接近和從事的知識,而是在大學講壇上傳授的學術了。
八世紀建立在牛頓力學之上的靜止的、機械的自然觀,進入到十九世紀初已有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則更有三大發(fā)現的產生,即細胞的發(fā)現、能量轉化的發(fā)現和達爾文進化論的發(fā)現。這一切,都向當時的德國哲學界提出了新的綜合的要求。
近代哲學的核心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而這個問題在德國古典哲學以前主要表現為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哲學家們都在以各種含混的方式力圖把自然和人調和起來。自然和人的原則只是在法國機械唯物論者和休謨那里才徹底暴露出其赤裸裸的本質,前者把一切人的東西都從自然身上剔除出去,只剩下非人的機械自然,后者則第一次用徹底的懷疑論和不可知論切斷了人和自然的真實聯(lián)系,使思維變成一種純粹主觀的、非存在性的東西。這就促使人們從自然和人的對立中發(fā)掘出真正本質的對立,即客體和主體兩大原則的對立。客體與主體的關系和自然與人的關系的區(qū)別在于,它不是僅僅著眼于外在呈現的靜止的兩種現象、兩件事物(自然界和人)的劃分,而是著眼于自然和人、精神和物質在行動中的相對關系,即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制約性的關系。在這里,思維和存在的關系不再像在自然和人的關系中那樣總是表現為兩種思維(人的思維和上帝的思維)或兩種存在(思維的存在和物質世界的存在)的外在關系,而是表現為絕對能動的思維主體和絕對必然的思維對象的不可分割的關系了,思維的主觀能動性取代上帝而成為了達到思維和存在、主體和客體的同一性之必要條件。因此,德國古典哲學對以往哲學的一個最顯著的超越,就在于對主體能動作用的有意識的強調,對理論和實踐的關系的高度重視,以及由此出發(fā)對自由和必然的關系問題的深入探討。
所以,德國古典哲學在它的創(chuàng)始人康德那里一開始就提出了主體和客體的最基本的同一性即認識的同一性是如何可能的問題。康德認為,認識是主體與客體的統(tǒng)一,即主體符合于客體;但主體如何能夠符合于客體?只有把客體理解為由主體自己建立起來的對象,即“現象”,主體才有可能認識這個客體、適合于這種客體。所以主體之所以符合客體首先還是由于客體是符合于主體的客體(而非自在的客體),即由先天的主體綜合經驗性的材料而造成的作為現象的對象。因此康德哲學的根本問題就是“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的問題。康德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人的知性先天地具有一種綜合統(tǒng)一感性經驗材料的本源的能力,即“先驗自我意識”的綜合機能,它能夠自發(fā)能動地憑借其十二范疇去統(tǒng)攝經驗雜多材料而形成先天綜合判斷,從而建構起人類科學知識的大廈。但這種能力只及于感性經驗的范圍,因而只及于現象界,卻不能達到自在之物。
與康德僅僅局限于認識領域片面地解決主體和客體問題不同,費希特把認識的主體和實踐的主體合為一體,將主體的能動性延伸到了自在之物的本體領域。這就提示謝林把立足點轉移到主體和客體的原始統(tǒng)一即“絕對同一”上來。
黑格爾則認為,從主體和客體的同一出發(fā)是對的,但是必須通過理性和邏輯,不過不是傳統(tǒng)的形式邏輯,而是能動的內容邏輯(辯證邏輯),這種邏輯的最本質的特點就是概念的自我否定性。所以絕對同一之所以發(fā)展出差異性,不是由于外來的影響,也不是由于神秘的力量,而只是由于“同一”這一概念的自我否定的本性,因為“同一”本身就意味著“與差異不同的東西”,因而是一種包含“不同”即差異于自身的東西。只有包含差異的同一才是真正自身能動的東西,它必然由于自身的差異而發(fā)展為內在的對立和矛盾,而形成一個東西自己運動的內在根據。所以在黑格爾看來,主體和實體(客體)完全是一個東西,兩者的同一不但體現為一個邏輯結構,而且實現為一個歷史過程;這種邏輯是運動和歷史的邏輯,而這種歷史則是有規(guī)律的、合乎邏輯的過程;自然界、人、社會歷史和精神生活的各種形態(tài)都成為了這一歷史過程中的各個不同階段,整個這一體系則構成了“絕對精神”的普遍實體。這就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宏大的方式,把主體和客體結合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體系,其中,主體是能動的靈魂,是推動萬物不斷超越自身的力量,但它又是合理的、合邏輯的,所以它能夠形成具有強大制約性的客體。但這客體又不是靜止不動的東西,而是內在地不安息的主體性的東西,它渴望創(chuàng)造奇跡,整個現實世界的等級系統(tǒng)都可以看作它按照一定程序一步步創(chuàng)造出來的。不過當它最后創(chuàng)造出黑格爾時代的現實時,它便到此止步了,它的主體能動性就被窒息在封閉的體系中了。可見整個黑格爾的體系是一個向后看的閉合體系,它沒有為未來的發(fā)展留下任何余地。
在這個封閉體系上炸開第一個缺口的是費爾巴哈,他所使用的炸藥則是感性。但經過了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洗禮,這種感性的人的原則和休謨的人性論已有了本質的不同,它已經不是個人的感覺,而是作為理性的根基的人“類”的感覺,因而能夠為自然科學提供最牢固的基礎;這種感性的自然的原則和法國唯物主義的自然原則也有了本質的不同,它已經不是非人的自然界,而是滲透著人本主義精神、在自然中保留了人的全面豐富的情感和美的自然主義了。然而,從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制約性這一對矛盾的角度來看,費爾巴哈并沒有作出更大的理論上的直接推進,而只是為進一步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和地基。因為他所理解的感性主要是“感性直觀”和“感性存在”,而沒有把感性從本質上理解為“感性活動”,即人的主體真正能動的現實社會活動。因而他把人的存在直接就當成了人的本質,離開人的可能性(自由的創(chuàng)造性)來談人的存在,最終使感性這種人的解放的要素成為了人的一種局限性和束縛。盡管如此,費爾巴哈的“感性的轉向”為后來的馬克思在新的基礎上解決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制約性的問題準備了前提,并從此使傳統(tǒng)哲學走出了形而上學封閉體系的慣性,而日益自覺地成為了開放系統(tǒng)上的一個個“路標”(海德格爾語)。由此可見,費爾巴哈(和馬克思)是從近代哲學向現代哲學轉向的一個關鍵的契機。
郵箱
huangbenjincv@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