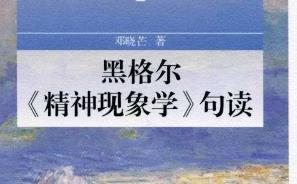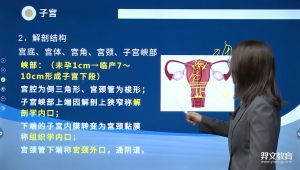- 1a
- 1b
- 2a
- 2b
- 3a
- 3b
- 4a
- 4b
- 5a
- 5b
- 6a
- 6b
- 7a
- 7b
- 8a
- 8b
- 9a
- 9b
- 10a
- 10b
- 11a
- 11b
- 12a
- 12b
- 13a
- 13b
- 14a
- 14b
- 15a
- 15b
- 16a
- 16b
- 17a
- 17b
- 18a
- 18b
- 19a
- 19b
- 20a
- 20b
- 21a
- 21b
- 22a
- 22b
- 23a
- 23b
- 24a
- 24b
- 25a
- 25b
- 26a
- 26b
- 27a
- 27b
- 28a
- 28b
- 29a
- 29b
- 30a
- 30b
- 31a
- 31b
- 32a
- 32b
- 33a
- 33b
- 34a
- 34b
- 35a
- 35b
- 36a
- 36b
- 37a
- 37b
- 38a
- 38b
- 39a
- 39b
- 40a
- 40b
- 41a
- 41b
- 42a
- 42b
- 43a
- 43b
- 44a
- 44b
- 45a
- 45b
- 46a
- 46b
- 47a
- 47b
- 48a
- 48b
- 49a
- 49b
- 50a
- 50b
- 51a
- 51b
- 52a
- 52b
- 53a
- 53b
- 54a
- 54b
- 55a
- 55b
- 56a
- 56b
- 57a
- 57b
- 58a
- 58b
- 59a
- 59b
- 60a
- 60b
- 61a
- 61b
- 62a
- 62b
- 63a
- 63b
- 64a
- 64b
- 65a
- 65b
- 66a
- 66b
- 67a
- 67b
- 68a
- 68b
- 69a
- 69b
- 70a
- 70b
- 71a
- 71b
- 72a
- 72b
- 73a
- 73b
- 74a
- 74b
- 75a
- 75b
- 76a
- 76b
- 77a
- 77b
- 78a
- 78b
- 79a
- 79b
- 80a
- 80b
- 81a
- 81b
- 82a
- 82b
- 83a
- 83b
- 84a
- 84b
- 85a
- 85b
- 86a
- 86b
- 87a
- 87b
- 88a
- 88b
- 89a
- 89b
- 90a
- 90b
- 91a
- 91b
- 92a
- 92b
- 93a
- 93b
- 94a
- 94b
- 95a
- 95b
- 96a
- 96b
- 97a
- 97b
- 98a
- 98b
- 99a
- 99b
- 100a
- 100b
- 101a
- 101b
- 102a
- 102b
- 103a
- 103b
- 104a
- 104b
- 105a
- 105b
- 106a
- 106b
- 107a
- 107b
- 108a
- 108b
- 109a
- 109b
- 110a
- 110b
- 111a
- 111b
- 112a
- 112b
- 113a
- 113b
- 114a
- 114b
- 115a
- 115b
- 116a
- 116b
- 117a
- 117b
- 118a
- 118b
- 119a
- 119b
- 120a
- 120b
- 121a
- 121b
- 122a
- 122b
- 123a
- 123b
- 124a
- 124b
- 125a
- 125b
- 126a
- 126b
- 127a
- 127b
- 128a
- 128b
- 129a
- 129b
- 130a
- 130b
- 131a
- 131b
- 132a
- 132b
- 133a
- 133b
- 134a
- 134b
- 135a
- 135b
- 136a
- 136b
- 137a
- 137b
- 138a
- 138b
- 139a
- 139b
- 140a
- 140b
- 141a
- 141b
- 142a
- 142b
- 143a
- 143b
- 144a
- 144b
- 145a
- 145b
鄧曉芒(1948一),湖南長(zhǎng)沙人,1964年初中畢業(yè)即下放農(nóng)村當(dāng)知青,10年后回城當(dāng)搬運(yùn)工。1979年考入武漢大學(xué)哲學(xué)系攻讀西方哲學(xué)史碩士研究生,1982年獲碩士學(xué)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評(píng)為教授,2010年起改任華中科技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現(xiàn)為中華外國(guó)哲學(xué)史學(xué)會(huì)常務(wù)理事,《德國(guó)哲學(xué)》主編,華中科技大學(xué)德國(guó)哲學(xué)研究中心主任。
鄧曉芒教授長(zhǎng)期從事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的翻譯與研究,又旁及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美學(xué)、中西哲學(xué)和文化比較、文藝?yán)碚摵臀膶W(xué)批評(píng)等,并積極介入社會(huì)批判和熱點(diǎn)問(wèn)題,創(chuàng)立了“新實(shí)踐美學(xué)”和“新批判主義”。目前已出版著作29部,譯著7部,發(fā)表學(xué)術(shù)論文兩百余篇,短評(píng)、序跋及文學(xué)評(píng)論一百余篇。
自2000年起,鄧曉芒教授在課堂上對(duì)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進(jìn)行句讀,歷經(jīng)七年,十四個(gè)學(xué)期,出版了近兩百萬(wàn)字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在完成對(duì)康德《實(shí)踐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學(xué)奠基》的句讀之后,于2010年開(kāi)設(shè)了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句讀的課程,授課的內(nèi)容形成了超過(guò)五百萬(wàn)字的十卷本《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句讀》,此外還句讀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學(xué)》的“德行論導(dǎo)論”部分。
慧田哲學(xué)按:截止2017年9月初,鄧曉芒老師的十卷本《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句讀》已全部出版,除了「嚴(yán)謹(jǐn)、深入、直譯與貫通」的專業(yè)翻譯理念之外,對(duì)哲學(xué)愛(ài)好者而言,無(wú)疑是一桌精神上的“滿漢全席”。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不同的是,《精神現(xiàn)象學(xué)》除了在訓(xùn)練人的思維,黑格爾還通過(guò)大量歷史文化知識(shí),以此切中人類的生存現(xiàn)實(shí),并試圖告訴我們:「我們天天面對(duì)的這個(gè)世界背后的深層運(yùn)作機(jī)理是什么?人如何才能把握到它并運(yùn)用到我們的生活中」?毋庸諱言,黑格爾要比康德難搞、難讀,康德旨在“讓理想照進(jìn)現(xiàn)實(shí)”,黑格爾卻要“讓現(xiàn)實(shí)變得更加真實(shí)”。本文鄧?yán)蠋熣劦降恼谴碎g差異和他近20年來(lái)做句讀工作的來(lái)龍去脈。文末,他依舊對(duì)腐朽學(xué)界表示咬牙切齒的痛恨:「到處都是圈子,沒(méi)有什么學(xué)派,只是宗派和幫派」!
趙立慶(以下簡(jiǎn)稱趙):請(qǐng)您先談?wù)勚螌W(xué)歷程,有哪些事件記憶尤為深刻?
鄧曉芒(以下簡(jiǎn)稱鄧):當(dāng)然是最開(kāi)始決定學(xué)習(xí)理論和哲學(xué)的時(shí)候,以我的初中學(xué)歷,這是根本不沾邊的事。
那是1969年,我21歲,已經(jīng)當(dāng)過(guò)五年下放知青了,當(dāng)時(shí)對(duì)人生、政治運(yùn)動(dòng)和國(guó)家前途感到極端的困惑,決心提高自己看問(wèn)題的水平。最初我找來(lái)一本最薄的理論小冊(cè)子,是列寧的《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中的左派幼稚病》,每個(gè)字都認(rèn)得,每句話都看得通,就是不知道在說(shuō)什么。我只好反復(fù)地看,一段一段地記筆記,把每一段的意思用自己的話寫(xiě)下來(lái),最后可以和知青朋友們把這本書(shū)的內(nèi)容講來(lái)——這時(shí)我覺(jué)得自己終于懂了。這是我讀懂的第一本理論書(shū),我都寫(xiě)在《我怎么學(xué)起哲學(xué)來(lái)》這篇文章中了,網(wǎng)上可查到。
趙:您的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句讀課程持續(xù)了9個(gè)學(xué)期共145講,這是一項(xiàng)巨大的工程。在此之前,您已經(jīng)完成了康德幾部重要著作的句讀或解讀,請(qǐng)問(wèn)這兩項(xiàng)工作之間有哪些聯(lián)系和區(qū)別?
鄧:我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康德哲學(xué)是中國(guó)人訓(xùn)練自己的理性思維能力的“夏令營(yíng)”,他留給后人的問(wèn)題是最多也最有價(jià)值的,要搞清這些問(wèn)題,甚至要進(jìn)入到這些問(wèn)題,沒(méi)有那種被康德提升到了“純粹理性”層次上來(lái)的思辨能力是根本沒(méi)有辦法的。但黑格爾完全不同,《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不是僅僅訓(xùn)練人的理性思維能力,而是對(duì)人的精神生活和人性各方面素質(zhì)的全面“教養(yǎng)”。康德的著作不一定需要對(duì)整個(gè)西方文化有全景式的了解也可以讀,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以及后來(lái)的《哲學(xué)百科全書(shū)》則不行,必須有相當(dāng)?shù)臏?zhǔn)備和廣博的知識(shí)面,或者說(shuō),這些著作能夠把人的思想極大地?cái)U(kuò)展到人類生存的各個(gè)方面,既訓(xùn)練人的思維,同時(shí)也將這種銳利的思維運(yùn)用于現(xiàn)實(shí)生活。這是康德的著作所不具備的,康德不管現(xiàn)實(shí),只是培養(yǎng)人的理想,告訴人應(yīng)當(dāng)做什么。黑格爾則告訴我們,你所面對(duì)的世界是怎樣的,如何發(fā)現(xiàn)它的本質(zhì)規(guī)律。讀黑格爾的書(shū)更需要哲學(xué)史的知識(shí)和一般歷史文化知識(shí)。
趙:您為什么選擇康德和黑格爾的著作進(jìn)行句讀?在黑格爾的著作中,為什么首先選取《精神現(xiàn)象學(xué)》進(jìn)行句讀?
鄧:《精神現(xiàn)象學(xué)》是黑格爾哲學(xué)成熟期的第一部著作,馬克思曾說(shuō)它是“黑格爾哲學(xué)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黑格爾后來(lái)的《哲學(xué)百科全書(shū)》中的每個(gè)環(huán)節(jié)在它里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來(lái)源,而且尚未受到邏輯范疇的嚴(yán)格規(guī)范,具有一種比較自然的關(guān)系。可以說(shuō),不懂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xué)》,就不知道黑格爾的《邏輯學(xué)》是從哪里來(lái)的。另一方面,黑格爾的這部著作又是他所有著作中最難讀懂的,不但中國(guó)人讀不懂,外國(guó)人也很少有人讀懂,一般都是從里面挑出幾段話來(lái)加以解釋和任意的發(fā)揮,而像這樣逐字逐句的系統(tǒng)解釋還從來(lái)沒(méi)有人做過(guò)。在我心目中,「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其他一些基本著作)是幫助中國(guó)人的思維上一個(gè)臺(tái)階的書(shū),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xué)》則是幫助我們?cè)谶@一臺(tái)階上登頂?shù)臅?shū)」,兩者都是中國(guó)人進(jìn)入到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界極其需要弄通的,否則你在國(guó)際上根木沒(méi)有發(fā)言權(quán)。
趙:句讀課程是面向怎樣的聽(tīng)眾的?如何協(xié)調(diào)教學(xué)與研究之間的關(guān)系?
鄧:一般我的句讀課都是給研究生和博士生開(kāi)設(shè)的“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原著選讀”課,但課堂永遠(yuǎn)是開(kāi)放的,準(zhǔn)都可以進(jìn)來(lái)找個(gè)位子坐下來(lái)聽(tīng),有事也可以隨時(shí)走人。本系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通常只有十幾二十人,但課堂里經(jīng)常有七、八十人,其他都是來(lái)“蹭課”的,有興趣濃厚的本科生,有外系的或外校的學(xué)生,甚至還有社會(huì)上的從業(yè)人員。有時(shí)還有每周從外地趕來(lái),聽(tīng)完課義趕火車(chē)回去的。
我常常對(duì)聽(tīng)眾說(shuō),你不需要聽(tīng)完整,只聽(tīng)其中一段也行;甚至也不需要完全聽(tīng)懂,重在聽(tīng)的過(guò)程,就是你看我怎么把一段一段“天書(shū)”一般的文字變成“人話”,聽(tīng)得多了,你今后也許就學(xué)會(huì)了如何理解西方經(jīng)典哲學(xué)著作的方法,而不至于對(duì)那些翻譯過(guò)來(lái)的句子望而生畏。所以我的課堂上不是傳授知識(shí),而是訓(xùn)練能力,就像一個(gè)武館,可以讓人打磨武功,即提高思維層次。因此我這里主要不是告訴學(xué)生一些現(xiàn)成的標(biāo)準(zhǔn)答案,而是展示一種做研究的方法,我曾把我的句讀課稱之為一種“口頭研究”,它甚至具有筆頭研究所不具備的長(zhǎng)處,就是思想的活潑和靈感的涌現(xiàn),有些見(jiàn)解和表達(dá)方式是坐在書(shū)齋里想不出來(lái)的。
趙:您是怎樣準(zhǔn)備每周一講的句讀課程的?是勻速進(jìn)行,還是會(huì)隨著原始文本難易程度來(lái)調(diào)整講授的節(jié)奏,在重點(diǎn)問(wèn)題上花更多的工夫?
鄧: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進(jìn)行的,《精神現(xiàn)象學(xué)》很少有不困難的地方,對(duì)于初接觸者來(lái)說(shuō),幾乎步步是障礙、處處是陷阱,偶爾有個(gè)別說(shuō)得明白或舉個(gè)通俗例子的地方,瞬間又被大量晦澀的思辨淹沒(méi)了。我每次講課三小時(shí),平均要準(zhǔn)備三天,有時(shí)講得順暢,可以一次講四到五個(gè)頁(yè)碼,不順暢時(shí)只能講三頁(yè)多一點(diǎn),就是這個(gè)進(jìn)度。所以網(wǎng)上有評(píng)論說(shuō)我的講課“好無(wú)聊”,這恐怕是實(shí)情,因?yàn)檫@里頭沒(méi)有什么激情或噱頭,只有老老實(shí)實(shí)地讀書(shū),就像你到少林寺去學(xué)武,成天就是那么幾個(gè)動(dòng)作,一下子是看不出什么成效來(lá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