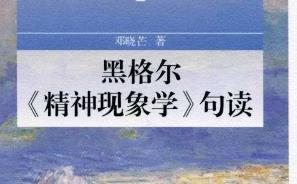貝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于1910年寫了這部著名的哲學導論,于1912年1月出版。此后,它曾經(jīng)被各個大學內(nèi)外好幾代的哲學學生所閱讀。本書屬于羅素最為豐產(chǎn)的哲學時期的作品之一。1910年他已經(jīng)完成了與A.N.懷特海(Whitehead)合作的巨著、也是現(xiàn)代數(shù)理邏輯的奠基石之一的Principia Mathematica(《數(shù)學原理》)所需要的冗長而又煩人的技術性工作。他說他的“心智始終沒有從這場緊張之下完全恢復過來”;然而在一般的哲學問題上,他顯然經(jīng)歷了一番新的生氣勃勃的解脫。雖然本書的寫作是作為一種通俗性的導論(羅素稱它是他的“廉價本的驚險小說”),但它卻提出了明確的觀點并引入了各種嶄新的觀念,例如論真理。它寫得是如此之明晰,毫不武斷而又流暢,清澈得光彩照人。它肯定值得永遠不斷地流傳。
羅素并沒有探討所有的哲學問題。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解說的,他把自己僅限于他認為自己可以肯定而且能有所建樹的那些問題。及時確定了自己的興趣之后,其結(jié)果便是這本主要是涉及知識論的書,即考察我們能說知道或有理由相信的那部分哲學分支。羅素在這一鉆研的基礎之上,還得出了某些令人矚目的有關所有事物的終極類別的結(jié)論。他并不探討倫理學以及有關心靈和行為的范圍廣大的各種經(jīng)典問題,諸如自我的本性或意志自由的問題。然而他的某些倫理觀卻表現(xiàn)在他所必須要談到的有關哲學的特性和價值問題之中——這個論題在全書之中反復出現(xiàn)過而在書尾則自成一章。
感覺數(shù)據(jù)、物理學與本能的信仰
羅素從對知覺的分析入手。表象乃是相對的:一張桌子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眼光看來就是不同的。但是我們并不認為桌子在變化。于是羅素就設定了他所謂的“感覺數(shù)據(jù)”。它們乃是“在感覺中直接被認知的事物”,“我們對它們有著直接的認知”(第4頁)。它們在變,盡管桌子并不變。在引入它們時,羅素也就區(qū)分了感知的一種行為(或狀態(tài))和它的對象。一種感知狀態(tài)乃是心靈的,而它的對象則可以是或者不是心靈上的。這就導致了第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點。因為掌握了這一區(qū)別(而這一點在全書中都將是重要的),羅素便可能得出結(jié)論說:當你從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視線感知到這同一張桌子時,你的感知對象乃是同一個,盡管構成你對它的覺察的那些經(jīng)驗是不同的。他很可能主張,你感知的對象乃是桌子,而不是它看上去的那種方式。但是他卻并沒有采取這種觀點;他使得它以你所看到它的那種方式而成為你的感知的對象;而他在它對你的心靈乃是私人所有,而且假如你不存在它也就不會存在的這種意義上,就把這一對象,亦即感覺數(shù)據(jù),當成了是你的心靈所私有的。假如你不存在的話,它也就不會存在。
那么,感覺數(shù)據(jù)和物理客體是什么關系呢?物理客體造成感覺數(shù)據(jù),物理學的目的就是要告訴我們,我們對于它們所能知道的一切。羅素終于在第3 章中得出結(jié)論說: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有關它們以及它們所占有的物理上的空間和時間,只不過是它們在關系上的結(jié)構,而并非它們內(nèi)在的性質(zhì)。但是首先,他提出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如果真實并非是它所呈現(xiàn)的那樣子,那么我們有沒有任何辦法知道究竟有沒有任何真實存在呢?而且如果是這樣,我們有沒有任何辦法來發(fā)見它究竟是什么樣子呢?”(第6頁)他認為這一點在邏輯上是可能的, 即我和我的經(jīng)驗與思想就是全部的存在。但是對物質(zhì)的常識上的信仰乃是本能,并且導致了最簡單的系統(tǒng)化的觀點,所以我們就可以接受它,哪怕我們承認它具有在邏輯上成為錯誤的可能性(第10—11頁)。
羅素繼續(xù)引出了一項教誡:
我們發(fā)見,一切知識都必須根據(jù)我們的本能信仰而建立起來,如果這些本能被否定,便一無所有了。但是在我們的本能信仰中,有些信仰比起別的要更有力得多;同時其中許多信仰由于習慣和聯(lián)想又和其它信仰糾纏在一起,這些其它信仰其實并不是本能的,只不過被人誤認為是本能信仰的一部分罷了。
哲學應該為我們指明本能信仰的層次,從我們所最堅持的那些信仰開始,并且盡可能把每種信仰都從不相干的附加物之中孤立出來,游離出來……一種本能信仰,除非和別的信仰相抵觸,否則就沒有任何理由不被接受;因此,如果發(fā)見它們可以彼此和諧,那么整個體系就是值得接受的。
當然,我們?nèi)康男叛龌蚱渲械娜魏我粭l都是可能錯誤的,因此,對一切信仰至少都應當稍有存疑。但是,除非我們以某種別的信仰為根據(jù),否則我們便不可能有理由拒絕一種信仰。(第11—12頁)
關于此處所列舉的羅素的方法,突現(xiàn)了兩點:
1.它在本質(zhì)上是訴之于本能的信仰之合理的權威性的。羅素并沒有簡單地訴之于最簡單的假定,無論是本能的或是其它的。在第6章中,他討論了歸納法, 他根本沒有提到最簡單的假說(或者“最好的解說”)之作為一種推論的方法。在第37頁他所說的歸納原則并不能讓我們從感覺數(shù)據(jù)推論到物理的客體。它只能允許我們推論到感覺數(shù)據(jù)之間的各種關系。
在這方面,他的方法屬于哲學中的一種非常英國式的傳統(tǒng),即19世紀特別是以湯瑪斯·萊德(注:萊德(Thomas Reid,1710—1796)英國哲學家。——譯者) 以及由小穆勒(注: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國哲學家。——譯者)(他生活的年代使他足以做羅素的祖父)為代表的一種非常有英國特色的傳統(tǒng)。所以注意到羅素的立場——與他的方法相反——是怎樣地與他們不同,是很引人入勝的。像羅素一樣,萊德肯定了本能的信仰以及對于物質(zhì)信仰的本能特性的權威性。然而他也非常深刻地批判了知覺“當前的”對象就是感覺數(shù)據(jù)、或者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觀念”的這一提法。他所采取的觀點就是我說過的羅素所可能采取的觀點——只要假定了他對觀察行為與其客體之間所做的區(qū)別的話。萊德對知覺的分析是非常有力的,很多哲學家在這一點上都會傾向采取他的觀點而反對羅素的那一方。
穆勒也同意本能信仰的權威性。也像羅素在本書(第11章)以及更早的萊德一樣,他認為記憶信仰乃是本能的,于是就接受了它們,將之作為權威性。但是與萊德和羅素不同,他論證說,對物質(zhì)的信念并不是本能的。它出自羅素在上面引的那段話里所認可的那種“習慣與聯(lián)想”。根據(jù)這些道理,穆勒就否認有任何理由可以認可物質(zhì)的存在,假如它被設想為是各種感覺的一種非精神的原因的話。反之,物質(zhì)卻應該被分解成為感覺的永恒可能性——這一立場與羅素本人后來(盡管只是暫時)所采取的立場非常相似。
2.但是我們?yōu)槭裁淳蛻撏饬_素(以及萊德和穆勒)說,如若一種信念是本能的,它就合理地是權威的呢?羅素并沒有提出這個問題,盡管他同意這一事實:一種信念是本能的,并不必定就是真的。他的態(tài)度和萊德的與穆勒的一樣:如果我們不接受本能信念的合理的(哪怕被宣告是無效的)權威,那么就全然沒有任何信念可以被認為是有效的了。對于一個絕對的懷疑派,是沒有什么可說的或者需要說的。
就此而言,這一點可能是對的,但是它卻留下了一個哲學的秘密。假設P 是某種操作,是羅素可以接受的,可以用來提煉我們本能的信念并加以系統(tǒng)化。那么他就要接受這一論點,即凡是一種延續(xù)P的本能的信仰,就是一種合理的信仰。又是什么使得那種信仰成為合理的呢?難道那僅只是由于我們本能地相信它么?人們確實可以希望對“本能性”與合理性之間顯然是至關重要的這種聯(lián)系再加以進一步的闡明。但是羅素也像在他以前的穆勒和萊德一樣,并沒有嘗試要這樣做。
唯心主義:認識的知識和描敘的知識
對唯心主義的批判(羅素在第19頁曾界定過它),是《哲學問題》中一個反復出現(xiàn)的論題。唯心主義在貝克萊、康德和黑格爾的書中多次提到過——對這些大不相同的哲學家,羅素是以大為不同的方式加以處理的。某些貝克萊的論據(jù),在第4 章中是解決得很有效的。羅素又得到了他對于心靈行為及其對象二者的區(qū)別,而且(或許是今人驚奇地設定了他本人對“感覺數(shù)據(jù)”的認可)運用它來反對貝克萊,那大抵上也就是萊德所采用的方式(第21—22頁)。此外,貝克萊對唯心主義的中心論據(jù)之一是說:“我們并不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任何事物的存在”(第22頁)。但是,正如羅素指出的:“‘知道’一詞在這里是用在兩種不同意義之上的”(第23頁)。有的知識是說某種情況,即有關真實性的知識,例如我對巴黎是法國的首都這種知識;但也有有關與真實性相對立的各種事物的知識。羅素稱這后一種知識為認識(acquaintance)。例如,我知道巴黎,那就是說我認識它,而我并不知道巴西利亞,哪怕我知道它是巴西的首都。正如羅素所說的,我們肯定能知道而且確實也知道存在著有某些客體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也就是說,有些客體是我們所不認識的。
這是對唯心主義所做的一個很好的論述,正如羅素所說它只是探討了維護唯心主義的許多論據(jù)之中的一種,而且它也并不特別新穎。然而在以下的一章(第5 章)中,探討卻有了一個新的轉(zhuǎn)折。羅素引入了描敘的知識這一概念。我可以說是由于描述而知道了一個客體的,假如我知道它是獨一無二地滿足了一種描述的話。例如我知道唯有巴西利亞才是滿足“巴西的首都”這一敘述的,所以我知道它乃是由于敘述,哪怕我由于認識(acquaintance)卻不知道它。由敘述而得的知識不同于由認識而得的知識,它是不能歸于認識了真相的。羅素說,我們只是認識“我們所直接感知的那些客體,而無需有任何推論過程的中介或者任何有關真相的知識”(第25頁)。這一點是他那知識論的一個重要部分——可以稱之為X論。根據(jù)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嚴格地說是體會到的、從而可以說是可知悉的,便是我們的感覺數(shù)據(jù)和我們自身。(第27—28頁)。所以我就不可能真正認識(acquainted)巴黎,而只不過是認識有關它的感覺數(shù)據(jù)而已。于是羅素就又增添了另一條重要的論題是有關認識與理解二者之間的聯(lián)系的:
我們所理解的每一個命題,都必定是全然是由我們所獲知的各種成分所組成的。
這個論題可以稱之為Y。由此可見,我們只能是對我們所熟悉的客體、 從而迄今為止也就是只對有關我們自身和我們的感覺數(shù)據(jù)作出判斷。然而哪怕是這一點也是不可能的,假如它們是我們所認知的唯一選項的話。因為要對一個選項作出一項判斷,乃是對它給定某種謂語;而要這樣做,我就必須熟悉某種被稱謂的東西。羅素把這些被稱謂的東西叫作共相。他那洞見之中有著一個非常重要而新穎的部分,即共相可以是任何數(shù)目的地方之間的各種關系。各種性質(zhì)只不過是一方面關系的特例。也可能有雙方的各種關系,像是a愛b,三方的關系,如a把b給了c,四方的關系,如a距離b比c距離d更遠,如此類推。
由X可見,我們必須是直接地感受到共相。所以羅素對我們直接所感知的一切的全部清單之中,就包含有我們自身、我們的感覺數(shù)據(jù)和共相。而其中唯有共相才是公共的,只有它們才可能是超出某一個人的認識以外的客體。這個客體以及X和Y就把羅素引到了我們可以談到的一些非常奇特的結(jié)論。例如,這就引導他達到了這一結(jié)論,即我們不可能肯定任何有關俾斯麥(注:俾斯麥(Otto von Bismasck 1815—1898)德國宰相。——譯者) 的問題。因為考慮一下“俾是一個狡黠的外交家”,這里的“俾”就是成其為俾斯麥的那個客體。唯有俾斯麥本人才可能判斷這一點。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多就是去描述這類的命題——例如,“有關其實際的對象乃是德帝國的宰相的這一命題就是說:這一對象是一個狡黠的外交家”(第31頁)。既已做出了這樣的一番描述,我們就可以判斷唯有能使它滿足的那個命題才是真的。僅只因為在這些描述中的共相乃是公共的,我們才能傳達。我們認識的任何其它客體,對于我們來說都是私有的。
我們不可能得出這樣奇怪的結(jié)論,即唯有俾斯麥才認識俾斯麥,假如是我們放棄無論是X還是羅素那限制性的學說的話,(即我們所能說的就是直接被覺察到的)一個與俾斯麥對話的人,難道不是“直接覺察到”俾斯麥的嗎?再者,關于任何通常說我可能認識的那種意義上,我所認識的乃是巴黎而不是巴西利亞。當然這與我覺察到的某種事實有著某種聯(lián)系。我熟悉巴黎是因為我曾經(jīng)到過那里,不是睡著而是意識到了我周圍的環(huán)境。Y也有某些值得稱道的地方,假如我們把它和通常有關認識的概念聯(lián)系到一起的話。例如,讓我們考慮一下這一陳述:“最長壽的人還沒有出世呢”。我可以斷言這話是真的。然而在一種很重要的意義上,它卻并不是一項有關確實對象(也就是活得最長壽的人)的判斷。因為假設我很知道腓德烈事實上將要成為壽命最長的人,那么我的判斷就是錯誤的;然而它確實并非是一個有關腓德烈的判斷——也就是我并沒有以一種顯然是謬誤的方式在判斷腓德烈,說他還沒有出生。另一方面,我肯定能夠做出有關腓德烈的各種判斷,乃是在這種意義上的——其他在若干世紀以前出世的人是不能做到的,盡管他們可以判斷說,最長壽的人還不曾出世呢。然則究竟是什么才能使一個人可以作出有關腓德烈的判斷呢?那個人必須熟識腓德烈么?假如是如此,那么又是在哪種意義上呢?這些問題以一種驚人的方式蔓延開來,并且一直在困擾著哲學家們。
自證、先驗與共相世界(第6—11章)
從第6章以下,羅素就考察我們是怎樣知道普遍原理的。首先他論證了歸納原理本身既不能被經(jīng)驗證明,也不能被否證;如其被人認知,它也必須是被它那“內(nèi)在的證據(jù)所認知”(第38頁)。歸納法也并非就是以這種方式為人所知的唯一的普遍原則。第7章又補充說,基本的邏輯原則也是內(nèi)在地清楚明白的, 或者說是“自明的”——確實,羅素的看法是它們要比歸納法有著更大程度的自明性。羅素使用了傳統(tǒng)的a priori[先驗或先天]一詞來指純粹基于其自明性、或者說我們由之而演繹出它們來的那種原理的自明性的普遍原則而具有的知識。他的意思是說,我們先于、或者說獨立于由經(jīng)驗所提供的證據(jù),就可以認識它們;雖說他同意經(jīng)驗可能是必要的,使得我們覺察到了它們。邏輯的原則也并非是我們先驗地所知道的唯一原則。倫理學(即關于什么是其本身就值得愿望的學說)的原則和數(shù)學的原則也是先天的。
在羅素的用語里,“先驗的”并不就等于“自明的”。因為一方面,某些先驗的原則并不是自明的。它們只是從那些成其為先天的原則之中推導出來的。另一方面,他也把僅只是陳述所賦認知者的都是些什么感覺數(shù)據(jù),歸入為自明的。此外,因為他認為記憶乃是對過去的感覺數(shù)據(jù)的直接感知,所以這些自明的真理也要包括記憶中所給定的有關感覺數(shù)據(jù)的各種真理。對這類真理的知識以及對邏輯、算學和倫理學的自明原理的先驗知識,也可以說是“直接的”或“直覺的”。其余的一切知識都是由“推導”而來的。
這種“當下的”、“直覺的”或“自明的”知識的觀念,有著很多艱深的難點,而羅素卻從來不曾很好地澄清過,盡管他在第11和第13章中做了一些嘗試。他提示說:
在“自明的”之中結(jié)合了兩種不同的概念……,其中之一符合于最高度的自明,確實是真理之不可動搖的保證,而另一種則在其余的各種程度上與之相適應,但卻并不能給出不可動搖的保證,只不過或多或少是一種推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