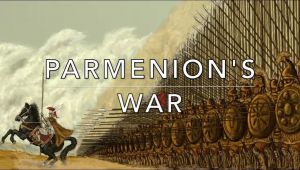對于一個新興的學科來說,初始的學術(shù)取向往往決定著學科的未來走向,初始的研究成績則影響著學科的基礎范式。民俗學是一門什么樣的學科?古代先賢并沒有為我們樹立一座指引航向的偉大燈塔,一切都有賴于民俗學者們摸著石頭過河。站在21世紀的今天回望90年前早期民俗學者們的學術(shù)規(guī)劃與學科理想,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和思考民俗學科的一些基本問題。
(中國民俗學運動歌)
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成立之后,1928年12月,顧頡剛、余永梁合作完成了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的《本所計劃書》,第四部分即“民俗”研究計劃,包括“作兩粵各地系統(tǒng)的風俗調(diào)查”、“西南各小民族材料之搜集”、“征求他省風俗,宗教,醫(yī)藥,歌謠,故事等材料”、“風俗模型之制造”、“鈔輯紙上之風俗材料”、“編制小說,戲劇,歌曲提要”、“編印民俗學叢書及”、“擴充風俗物品陳列室為歷史博物館民俗部”、“養(yǎng)成民俗學人才”九個方面。這個計劃比較全面,反映的是顧頡剛們對民俗學理想狀態(tài)的一種憧憬。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顧頡剛對民俗學的理解幾乎完全沒有涉及對國外民俗學理論和方法的借鑒,反倒像是胡適“整理國故”的具體落實。
在顧頡剛、容肇祖等人相繼離開中大之后,原民俗學會主席容肇祖的繼任者何思敬為“民俗學組”擬定了一個新的工作計劃,這一計劃與顧頡剛《本所計劃書》中的設想可說是截然相反,似乎完全是以西學為取向。到1932年底朱希祖接任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主任的時候,他并沒有沿用“民俗學組”這個名稱,而是重新舉起了“民俗學會”的大旗,請回了已經(jīng)到暨南大學任教的容肇祖再次出任中山大學民俗學會主席。這一時期“文史學研究所民俗學會”也制定了工作大綱。大綱中計劃顯得低調(diào)、務實,而且明顯是折衷了顧頡剛與何思敬的計劃。
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幾份工作計劃可以看出不同民俗學倡導者對于民俗學的理解以及工作計劃相去甚遠,反映出民俗學與國學、西學之間的復雜關系。
“民俗學”的提出與西學的關系
中國現(xiàn)代民俗學的提出,和西學具有密切關系,它從一開始就明確是對歐洲folklore的響應和移植,并由周作人從日本借用來“民俗學”這一譯名。而在中國,經(jīng)過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學術(shù)的形式與內(nèi)容出現(xiàn)重大而明顯的變化。形式上,以經(jīng)學為主導的傳統(tǒng)學術(shù)格局最終解體,受此制約的各學科分支按照現(xiàn)代西學分類相繼獨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支。這一時期的民俗學還談不上學科建設,甚至連民俗學到底是什么樣的一門學科都還是一頭霧水。
在英國,當時民俗學也還算不上一門獨立、成型的學科,所用的理論和方法也大多采自于人類學,但周作人等一批先行者卻急不可待地把它引入了中國。而常惠、顧頡剛等一批年輕學者所理解的中國民俗學與歐洲源頭的民俗學本不是一回事,他們想象的中國民俗學是一門研究民間風俗、信仰,以及流行文化的學問,是對平民文化的一種關注。他們強烈地意識到了民俗學與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的互補作用,以及民俗學在社會歷史研究格局中的重要性,因而極力地為之鼓吹。
當時把民俗學納入西學的一個重要作用是,西學在當時是一面旗幟,強調(diào)反叛傳統(tǒng)的五四新文化人有必要利用這一旗幟來作為號召,因為他們總是處在這樣一種尷尬之中:“為了與復古派劃清界限,不便理直氣壯地發(fā)掘并表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至于具體論述中,傾向于以西學剪裁中國文化,更是很難完全避開的陷阱。”所以鐘敬文先生說:“積極吸收外國先進理論與方法,是我國民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tǒng)。但我們在學習國外理論時,生搬硬套也使我們吃了不少苦頭。”
國學研究的興盛對民俗學的影響
清末民初,傳統(tǒng)經(jīng)學的宗主地位被打破,在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學界參照現(xiàn)代西方的學科格局重新洗牌,一批新的學科在西方學術(shù)的直接影響下應運而生,民俗學及其相關的人文學科如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方言學、考古學等一批新學科均在這一背景下誕生。
中國現(xiàn)代民俗學被提倡的時候,正是近代國學研究的轉(zhuǎn)型時期。由于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胡適等人的極力鼓吹,“國學”成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學術(shù)時尚。國學概念的提出是在20世紀初期,胡適對國學范圍的界定非常寬泛,認為國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凡“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shù)之大,下至一個字,一只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于國學研究的范圍”,明確說明即便如“山歌”一類的非經(jīng)史材料也可算做國學研究的對象。
在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的影響下,在胡適“科學方法”的啟迪下,顧頡剛以其天才的學術(shù)洞察力和學術(shù)創(chuàng)造力,對孟姜女故事進行研究,創(chuàng)立了中國民俗學最初的,也是沿用至今的、影響最大的研究范式——“歷史演進法”。顧頡剛最初寫作《孟姜女故事的轉(zhuǎn)變》的時候,所用的完全是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考證法。顧頡剛的杰出成就與其說是應用歐洲學術(shù)方法的結(jié)果,不如說是近現(xiàn)代國學轉(zhuǎn)型的產(chǎn)物。
把顧頡剛的學術(shù)淵源歸于國學,并不是要排斥西方學術(shù)的影響,或者說,這里所指的國學,不是一般意義上理解的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的簡單延續(xù),而是中國學術(shù)在近代西學影響下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過渡形態(tài)。桑兵在《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曾總結(jié)近現(xiàn)代國學研究在歐美日本漢學發(fā)展趨勢的影響下,學術(shù)風格與重心實現(xiàn)了三個方面的轉(zhuǎn)變:1.材料資取由單一的專注于文獻轉(zhuǎn)向了文本文獻、考古發(fā)掘、實物材料、口傳文化等多元材料的綜合運用。2.研究對象由專注于上層貴族的精英正統(tǒng)下移到民間地方社會。3.學科建設體現(xiàn)了不同學科的互動與整合。如果把這三項轉(zhuǎn)變當作近現(xiàn)代國學研究轉(zhuǎn)型的重要表征,再與現(xiàn)代民俗學的建設歷程兩相對照,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民俗學的發(fā)生正是這樣一種轉(zhuǎn)變的結(jié)果。
(歌謠周刊)
民俗學運動與現(xiàn)代國學運動的密切關系還可以通過一些更為直接現(xiàn)象來認識:
1.歌謠研究會、風俗調(diào)查會都是國學門下的分支機構(gòu),它們的全稱分別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歌謠研究會”“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風俗調(diào)查會”。
2.《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乃由《歌謠》周刊擴張而來。該刊以及后來的月刊“發(fā)表的民俗學方面的文章亦占有很大的比重,民間文學作品較少,而民俗學研究文章較多……研究涉及的面很廣。”
3.歌謠研究會的發(fā)起人都是國學門教授,如主要發(fā)起人沈兼士即為國學門主任。
4.由沈兼士、顧頡剛等人在廈門大學組織成立的“風俗調(diào)查會”,同樣是隸屬于該校國學院。
5.由傅斯年、顧頡剛創(chuàng)辦的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本質(zhì)上也是一個“國學”大本營,正如香港學者陳云根所說:“廣州的國立中山大學1924年由國民黨創(chuàng)建,享有大量的財政資助,在全國范圍內(nèi)扮演著高等黨校的角色,因此自然特別強調(diào)‘國學’。中山大學確定了國粹主義及由孫中山統(tǒng)一全中華的總路線,這極大地鼓舞了民俗學家們的研究熱情。”
6.中國現(xiàn)代民俗學的早期建設者顧頡剛、容肇祖、董作賓諸人,都被學界視作“國學大師”。
鐘敬文先生把中國現(xiàn)代民俗學的國學底色及其優(yōu)勢說得更加具體:“中國典籍豐富,又有考據(jù)傳統(tǒng),因此,考據(jù)便成了中國民俗學的一大特色。無論哪位學者,也無論他使用過怎樣的方法,在他的著作中,幾乎都會程度不同地留有考據(jù)學的身影,這就是獨具特色的中國民俗學。”對借鑒西學,鐘敬文表述了這樣的原則:“學術(shù)的最高境界在于對自身文化的準確把握,而不是對國外理論的刻意模仿。這就要求我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用踏實的調(diào)查,深入的分析,去實實在在地解決幾個問題。”他自己所走的學術(shù)路子也說明了這一點,“從他討論歌謠的第一篇文章《讀<粵東筆記>》開始,其所走的學術(shù)路子基本上就是古典文獻的研究和民俗學材料的分析相結(jié)合的思路,而且這也是當時《歌謠》周刊上發(fā)表的多數(shù)文章的共同特征。”
從早期民俗學研究的事實和民俗學者對學科的認識看出,民俗學并未偏離國學的范疇,民俗學正是一門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