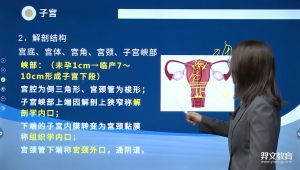- 《我的家》作者 季羨林
- 《談老年》作者 季羨林
- 《鄰人》作者季羨林
- 《生命的價值》作者 季羨林
- 《糊涂一點,瀟灑一點》季羨林 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
- 《生活的現(xiàn)實》作者 季羨林
- 《人間自有真情在》作者 季羨林
- 《兒時的事》作者:季羨林 留下了一個終生難補的心靈傷痕
- 《永久的悔》作者 季羨林
- 《九十五歲初度》作者季羨林
- 《容忍》作者:季羨林 誦讀:春天的風
- 《我寫我》作者季羨林
- 《成功》作者:季羨林 成功的三個條件和三種境界
- 《聽雨》 作者:季羨林
- 《忘》作者 季羨林
- 《我的女房東》作者季羨林
- 《談老年》作者季羨林
- 《爽朗的笑聲》,作者季羨林,一代人刻骨銘心的記憶
- 《永久的悔》作者:季羨林
- 《枸杞樹》/ 作者:季羨林 ;朗誦:黃小平
- 《做人與處世》作者季羨林,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 《聽雨》作者 季羨林
- 《黃昏》作者:季羨林
- 《我的妻子》作者季羨林
- 《時間》,作者:季羨林
- 《謙虛與虛偽》作者:季羨林 心安即是歸處
- 《壞人是不會變好的》作者季羨林
- 《心安即是歸處》做真實的自己!
- 《海棠花》作者:季羨林,誦讀:微讀時光
- 《壞人是不會變好的》,作者季羨林
在蕓蕓眾生中,有一種人,就是像我這樣的教書匠,或者美其名,稱之為“學者”。我們這種人難免不時要舞筆弄墨,寫點文章的。根據我的分析,文章約而言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被動寫的文章,一是主動寫的文章。
所謂“被動寫的文章”,在中國歷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的應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這種文章多半是“代圣人立言”的,或者是“頌圣”的,不許說自己真正想說的話。換句話說,就是必須會說廢話。記得魯迅在什么文章中舉了一個廢話的例子:“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實中懷之在抱。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后面好像還有,我記不清楚了。)這是典型的廢話,念起來卻聲調鏗鏘。“試帖詩”中也不乏好作品,唐代錢起詠湘靈鼓琴的詩,就曾被朱光潛先生贊美過,而朱先生的贊美又被魯迅先生諷刺過。到了今天,我們被動寫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見。我們寫的廢話,說的謊話,吹的大話,也是到處可見的。我覺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寫的,有好些書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這樣的文章,出版這樣的書,則必然能夠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紙張;對保護環(huán)境,保持生態(tài)平衡,會有很大的好處的;對人類生存的前途也會減少危害的。
至于主動寫的文章,也不能一概而論。仔細分析起來,也是五花八門的,有的人為了提職,需要提交“著作”,于是就趕緊炮制;有的人為了成名成家,也必須有文章,也努力炮制。對于這樣的人,無須深責,這是人之常情。炮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優(yōu)秀的東西,像吾輩“爬格子族”的人們,非主動寫文章以賺點稿費不行,只靠我們的工資,必將斷炊。我輩被“尊”為教授的人,也不例外。
在中國學術界里,主動寫文章的學者中,有不少的人學術道德是高尚的。他們專心一致,唯學是務,勤奮思考,多方探求,寫出來的文章盡管有點參差不齊;但是他們都是值得欽佩、值得贊美的,他們是我們中國學術界的脊梁。
真正的學術著作,約略言之,可以分為兩大類:單篇的論文與成本的專著。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古今中外的許多大部頭的專著,像中國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等,都是名垂千古、輝煌璀璨的巨著,是我們國家的瑰寶。這里不再詳論。我要比較詳細地談一談單篇論文的問題。單篇論文的核心是講自己的看法、自己異于前人的新意,要發(fā)前人未發(fā)之覆。有這樣的文章,學術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發(fā)展。如果寫一部專著,其中可能有自己的新意,也可能沒有。因為大多數的專著是綜合的、全面的敘述。即使不是自己的新意,也必須寫進去,否則就不算全面。論文則沒有這種負擔,它的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而是有新意,它與專著的關系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
我在上面幾次講到“新意”,“新意”是從哪里來的呢?有的可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出于“靈感”的,比如傳說中牛頓因見蘋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但我們必須注意,這種靈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牛頓一定是很早就考慮這類的問題,晝思夜想,一旦遇到相應的時機,便豁然頓悟。吾輩平凡的人,天天吃蘋果,只覺得它香脆甜美,管它什么勞什子“地心吸力”干嗎!在科學技術史上,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來,現(xiàn)在先不去談它了。
在以前極左思想肆虐的時候,學術界曾大批“從雜志縫里找文章”的做法,因為這樣就不能“代圣人立言”;必須心中先有一件先入為主的教條的東西要宣傳,這樣的文章才合乎程式。有“學術新意”是觸犯“天條”的。這樣的文章一時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這樣的文章印了出來,再當做垃圾賣給收破爛的(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白色垃圾”),除了浪費紙張以外,絲毫無補于學術的進步。我現(xiàn)在立一新義: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到雜志縫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頭的專著中,在字里行間,也能找到新意的,舊日所謂“讀書得間”,指的就是這種情況。因為,一般說來,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往往只談一個問題、一個新問題,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讀過以后,受到啟發(fā),舉一反三,自己也產生了新意,然后寫成文章,讓別的學人也受到啟發(fā),再舉一反三。如此往復循環(huán),學術的進步就寓于其中了。
可惜——是我覺得可惜——眼前在國內學術界中,讀雜志的風氣,頗為不振。不但外國的雜志不讀,連中國的雜志也不看。閉門造車,焉得出而合轍?別人的文章不讀,別人的觀點不知,別人已經發(fā)表過的意見不聞不問,只是一味地寫去寫去。這樣怎么能推動學術前進呢?更可怕的是,這個問題幾乎沒有人提出。有人空喊“同國際學術接軌”。不讀外國同行的新雜志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軌”究竟在哪里嗎?連“軌”在哪里都不知道,空喊“接軌”,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1997年
賦得了永久的悔
我出生在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里。我們家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家里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按照當時的標準,吃“白的”(指麥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顏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白的”與我們家無緣。“黃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顏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終日為伍者只有“紅的”。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兒談“紅”色變了。
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動換來的。一到夏天麥收季節(jié),我們家根本沒有什么麥子可收。對門住的寧家大嬸子和大姑——她們家也窮得夠戧——就帶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麥子”。所謂“拾麥子”就是別家的長工割過麥子,總還會剩下那么一點兒麥穗,這些都是不值得一撿的,我們這些窮人就來“拾”。因為剩下的決不會多,我們拾上半天,也不過拾半籃子;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已經是如獲至寶了。
記得有一年,我拾麥子的成績也許是有點“超常”。到了中秋節(jié)——農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親不知從哪里弄來點兒月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起來。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好東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上一次。我當時并沒有注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xiàn)在回想起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不但是月餅,連其他“白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嘗過,都留給我吃了。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的高粱餅子為伍。到了歉年,連這個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白的”和月餅難得,“黃的”怎樣呢?“黃的”也同樣難得。但是,盡管我只有幾歲,我卻也想出了辦法。到了春、夏、秋三個季節(jié),莊外的草和莊稼都長起來了。我就到莊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葉。劈高粱葉,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還歡迎;因為葉子一劈,通風情況就能改進,高粱長得就能更好,糧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葉都是喂牛用的。我們家窮,從來沒有養(yǎng)過牛。我二大爺家是有地的,經常養(yǎng)著兩頭大牛。我這草和高粱葉就是給它們準備的。每當我這個不到三塊豆腐干高的孩子背著一大捆草或高粱葉走進二大爺的大門,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賴著不走,總能蹭上一頓“黃的”吃,不會被二大娘“卷”(我們那里的土話,意思是“罵”)出來。到了過年的時候,自己心里覺得,在過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氣到二大爺家里賴著吃黃面糕。黃面糕是用黃米面加上棗蒸成的,顏色雖黃,卻位列“白的”之上,因為一年只在過年時吃一次,物以稀為貴,于是黃面糕就貴了起來。
我上面講的全是吃的東西。為什么一講到母親就講起吃的東西來了呢?原因并不復雜。第一,我作為一個孩子容易關心吃的東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東西,幾乎都與母親無緣。除了“黃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邊兒。我在她身邊只呆到6歲,以后兩次奔喪回家,呆的時間也很短。現(xiàn)在我回憶起來,連母親的面影都是迷離模糊的,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特別有一點,讓我難解而又易解: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母親的笑容來,她好像是一輩子都沒有笑過。家境貧困,兒子遠離,她受盡了苦難,笑容從何而來呢?有一次我回家聽對面的寧大嬸子告訴我說:“你娘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他走的!”簡短的一句話里面含著多少辛酸、多少悲傷啊!母親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遠方,盼望自己的兒子回來啊!然而這個兒子卻始終沒有歸去,一直到母親離開這個世界。
對于這個情況,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時候,自己大了幾歲,逐漸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籬下,經濟不能獨立,空有雄心壯志,怎奈無法實現(xiàn),我暗暗地下定了決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學畢業(yè),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養(yǎng)母親;然而沒有等到我大學畢業(yè),母親就離開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yǎng)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親臨終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當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世界上無論什么名譽,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榮,都比不上呆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
月是故鄉(xiāng)明
每個人都有個故鄉(xiāng),人人的故鄉(xiāng)都有個月亮。人人都愛自己故鄉(xiāng)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個月亮,未免顯得有點孤單。因此,在中國古詩文中,月亮總有什么東西當陪襯,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印月”等等,不可勝數。
我的故鄉(xiāng)是在山東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時候,從來沒有見過山,也不知山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個圓而粗的柱子吧,頂天立地,好不威風。以后到了濟南,才見到山,恍然大悟:原來山是這個樣子呀!因此,我在故鄉(xiāng)里望月,從來不同山聯(lián)系。像蘇東坡說的“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完全是我無法想像的。
至于水,我的故鄉(xiāng)小村卻大大地有。幾個小葦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在我這個小孩子眼中,雖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那樣有氣派,但也頗有一點煙波浩渺之勢。到了夏天,黃昏以后,我在坑邊的場院里躺在地上,數天上的星星。有時候在古柳下面點起篝火,然后上樹一搖,成群的知了飛落下來,比白天用嚼爛的麥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樂此不疲,天天盼望黃昏早早來臨。
到了更晚的時候,我走到坑邊,抬頭看到晴空一輪明月,清光四溢,與水里的那個月亮相映成趣。我當時雖然還不懂什么叫詩興,但也顧而樂之,心中油然有什么東西在萌動。有時候在坑邊玩很久,才回家睡覺。在夢中見到兩個月亮疊在一起。清光更加晶瑩澄澈。第二天一早起來,到坑邊葦子叢里去撿鴨子下的蛋,白白地一閃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個蛋。此時更是樂不可支了。
我只在故鄉(xiāng)呆了六年,以后就離鄉(xiāng)背井漂泊天涯。在濟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過四年,又回到濟南呆了一年,然后在歐洲住了十一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現(xiàn)在已經十多年了。在這期間,我曾到過世界上將進三十個國家,我看過許許多多的月亮。在風光旖旎的瑞士萊芒湖上,在平沙無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萬頃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過月亮。這些月亮應該說都是美妙絕倫的,我都異常喜歡。但是,看到他們,我立刻就想到我故鄉(xiāng)中那個葦坑上面和水中的那個小月亮。對比之下,無論如何我也感到,這些廣闊世界的大月亮,萬萬比不上我那心愛的小月亮。不管我離開我的故鄉(xiāng)多少萬里,我的心立刻就飛來了。我的小月亮,我永遠忘不掉你!
我現(xiàn)在已經年近耄耋,住的朗潤園勝地。夸大一點說,此地有茂林修竹,綠水環(huán)流,還有幾座土山,點綴其間。風光無疑是絕妙的。前幾年,我從廬山休養(yǎng)回來,一個同在廬山休養(yǎng)的老朋友來看我。他看到這樣的風光,慨然說:“你住在這樣的好地方,還到廬山去干嘛呢!”可見朗潤園給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樹,有花,有鳥,每逢望夜,一輪當空,月光閃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一碧數頃,而且荷香遠溢,宿鳥幽鳴,真不能不說是賞月勝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誰來到這里,難道還能不顧而樂之嗎?
然而,每值這樣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仍然是故鄉(xiāng)葦坑里的那個平凡的小月亮。見月思鄉(xiāng),已經成為我經常的經歷。思鄉(xiāng)之病,說不上是苦是樂,其中有追憶,有惆悵,有留戀,有惋惜。流光如逝,時不再來。在微苦中實有甜美在。
月是故鄉(xiāng)明,我什么時候能夠再看到我故鄉(xiāng)的月亮呀!我悵望南天,心飛向故里。
神奇的絲瓜
今年春天,孩子們在房前空地上,斬草挖土,開辟出來了一個一丈見方的小花園。周圍用竹竿扎了一個籬笆,移來了一棵玉蘭花樹,栽上了幾株月季花,又在竹籬下面隨意種上了幾棵扁豆和兩棵絲瓜。土壤并不肥沃,雖然也鋪上了一層河泥,但估計不會起很大的作用,大家不過是玩玩而已。
過了不久,絲瓜竟然長了出來,而且日益茁壯、長大。這當然增加了我們的興趣。但是我們也并沒有過高的期望。我自己每天早晨工作疲倦了,常到屋旁的小土山上走一走,站一站,看看墻外馬路上的車水馬龍和亞運會招展的彩旗,顧而樂之,只不過順便看一看絲瓜罷了。
絲瓜是普通的植物,我也并沒有想到會有什么神奇之處。可是忽然有一天,我發(fā)現(xiàn)絲瓜秧爬出了籬笆,爬上了樓墻。以后,每天看絲瓜,總比前一天向樓上爬了一大段;最后竟從一樓爬上了二樓,又從二樓爬上了三樓。說它每天長出半尺,決非夸大之詞。絲瓜的秧不過像細繩一般粗,如不注意,連它的根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這樣細的一根秧竟能在一夜之間輸送這樣多的水分和養(yǎng)料,供應前方,使得上面的葉子長得又肥又綠,爬在灰白色的墻上,一片濃綠,給土墻增添了無量活力與生機。
這當然讓我感到很驚奇,我的興趣隨之大大地提高。每天早晨看絲瓜成了我的主要任務,爬小山反而成為次要的了。我往往注視著細細的瓜秧和濃綠的瓜葉,陷入沉思,想得很遠,很遠……
又過了幾天,絲瓜開出了黃花。再過幾天,有的黃花就變成了小小的綠色的瓜。瓜越長越長,越長越長,重量當然也越來越增加,最初長出的那一個小瓜竟把瓜秧墜下來了一點,直挺挺地懸垂在空中,隨風搖擺。我真是替它擔心,生怕它經不住這一份重量,會整個地從樓上墜了下來落到地上。
然而不久就證明了,我這種擔心是多余的。最初長出來了的瓜不再長大,仿佛得到命令停止了生長。在上面,在三樓一位一百零二歲的老太太的窗外窗臺上,卻長出來兩個瓜。這兩個瓜后來居上,發(fā)瘋似地猛長,不久就長成了小孩胳膊一般粗了。這兩個瓜加起來恐怕有五六斤重,那一根細秧怎么能承擔得住呢?我又擔心起來。沒過幾天,事實又證明了我是杞人憂天。兩個瓜不知從什么時候忽然彎了起來,把軀體放在老太太的窗臺上,從下面看上去,活像兩個粗大彎曲的綠色牛角。
不知道從哪一天起,我忽然又發(fā)現(xiàn),在兩個大瓜的下面,在二三樓之間,在一根細秧的頂端,又長出來了一個瓜,垂直地懸在那里。我又犯了擔心病:這個瓜上面夠不到窗臺,下面也是空空的;總有一天,它越長越大,會把上面的兩個大瓜也墜了下來,一起墜到地上,落葉歸根,同它的根部聚合在一起。
然而今天早晨,我卻看到了奇跡。同往日一樣,我習慣地抬頭看瓜:下面最小的那一個早已停止生長,孤零零地懸在空中,似乎一點分量都沒有;上面老太太窗臺上那兩個大的,似乎長得更大了,威武雄壯地壓在窗臺上;中間的那一個卻不見了。我看看地上,沒有看到掉下來的瓜。等我倒退幾步抬頭再看時,卻看到那一個我認為失蹤了的瓜,平著身子躺在抗震加固時筑上的緊靠樓墻凸出的一個臺子上。這真讓我大吃一驚。這樣一個原來垂直懸在空中的瓜怎么忽然平身躺在那里了呢?這個凸出的臺子無論是從上面還是從下面都是無法上去的,決不會有人把絲瓜擺平的。
我百思不得其解,徘徊在絲瓜下面,像達摩老祖一樣,面壁參禪。我仿佛覺得這棵絲瓜有了思想,它能考慮問題,而且還有行動,它能讓無法承擔重量的瓜停止生長;它能給處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擔重量的地方,給這樣的瓜特殊待遇,讓它們瘋狂地長;它能讓懸垂的瓜平身躺下。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無論如何也無法解釋我上面談到的現(xiàn)象。但是,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又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絲瓜用什么來思想呢?絲瓜靠什么來指導自己的行動呢?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從來也沒有人說過,絲瓜會有思想。我左考慮,右考慮;越考慮越糊涂。我無法同絲瓜對話,這是一個沉默的奇跡。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繩子,綠葉上照舊濃翠撲人眉宇。我站在絲瓜下面,陷入夢幻。而絲瓜則似乎心中有數,無言靜觀,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笑面對秋陽。
清塘荷韻
樓前有清塘數畝。記得三十多年前初搬來時,池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記憶里還殘留著一些綠葉紅花的碎影。后來時移事遷,歲月流逝,池塘里卻變得“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見什么荷花了。
我腦袋里保留的舊的思想意識頗多,每一次望到空蕩蕩的池塘,總覺得好像缺點什么。這不符合我的審美觀念。有池塘就應當有點綠的東西,哪怕是蘆葦呢,也比什么都沒有強。最好的最理想的當然是荷花。中國舊的詩文中,描寫荷花的簡直是太多太多了。周敦頤的《愛蓮說》讀書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遠益清”是膾炙人口的。幾乎可以說,中國沒有人不愛荷花的。可我們樓前池塘中獨獨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總覺得是一塊心病。
有人從湖北來,帶來了洪湖的幾顆蓮子,外殼呈黑色,極硬。據說,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夠千年不爛。因此,我用鐵錘在蓮子上砸開了一條縫,讓蓮芽能夠破殼而出,不至永遠埋在泥中。這都是一些主觀的愿望,蓮芽能不能夠出,都是極大的未知數。反正我總算是盡了人事,把五六顆敲破的蓮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聽天命了。
這樣一來,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邊上去看上幾次。心里總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綠的蓮葉長出水面。可是,事與愿違,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涼落葉,水面上也沒有出現(xiàn)什么東西。經過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綠柳垂絲,一片旖旎的風光。可是,我翹盼的水面上卻仍然沒有露出什么荷葉。此時我已經完全灰了心,以為那幾顆湖北帶來的硬殼蓮子,由于人力無法解釋的原因,大概不會再有長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無法把荷葉從淤泥中吸出。
但是,到了第三年,卻忽然出了奇跡。有一天,我忽然發(fā)現(xiàn),在我投蓮子的地方長出了幾個圓圓的綠葉,雖然顏色極惹人喜愛;但是卻細弱單薄,可憐兮兮地平臥在水面上,像水浮蓮的葉子一樣。而且最初只長出了五六個葉片。我總嫌這有點太少,總希望多長出幾片來。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邊上去觀望。有校外的農民來撈水草,我總請求他們手下留情,不要碰斷葉片。但是經過了漫漫的長夏,凄清的秋天又降臨人間,池塘里浮動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個葉片。對我來說,這又是一個雖微有希望但究竟仍令人灰心的一年。
真正的奇跡出現(xiàn)在第四年上。嚴冬一過,池塘里又溢滿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長葉的時候,在去年飄浮著五六個葉片的地方,一夜之間,突然長出了一大片綠葉,而且看來荷花在嚴冬的冰下并沒有停止行動,因為在離開原有五六個葉片的那塊基地比較遠的池塘中心,也長出了葉片。葉片擴張的速度,擴張范圍的擴大,都是驚人地快。幾天之內,池塘內不小一部分,已經全為綠葉所覆蓋。而且原來平臥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蓮一樣的葉片,不知道是從哪里聚集來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躍出了水面,長成了亭亭的荷葉。原來我心中還遲遲疑疑,怕池中長的是水浮蓮,而不是真正的荷花。這樣一來,我心中的疑云一掃而光:池塘中生長的真正是洪湖蓮花的子孫了。我心中狂喜,這幾年總算是沒有白等。
天地萌生萬物,對包括人在內的動植物等有生命的東西,總是賦予一種極其驚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極其驚人的擴展蔓延的力量,這種力量大到無法抗御。只要你肯費力來觀摩一下,就必然會承認這一點。現(xiàn)在擺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樓前池塘里的荷花。自從幾個勇敢的葉片躍出水面以后,許多葉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間,就出來了幾十枝,而且迅速地擴散、蔓延。不到十幾天的工夫,荷葉已經蔓延得遮蔽了半個池塘。從我撒種的地方出發(fā),向東西南北四面擴展。我無法知道,荷花是怎樣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動。反正從露出水面荷葉來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離,才能形成眼前這個局面。
光長荷葉,當然是不能滿足的。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據了解荷花的行家說,我門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園其他池塘里的,都不一樣。其他地方的荷花,顏色淺紅;而我這里的荷花,不但紅色濃,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開出十六個復瓣,看上去當然就與眾不同了。這些紅艷耀目的荷花,高高地凌駕于蓮葉之上,迎風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時讀舊詩:“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愛其詩句之美,深恨沒有能親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賞一番。現(xiàn)在我門前池塘中呈現(xiàn)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把西湖從杭州搬到燕園里來了。豈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幾年才搬到朗潤園來的周一良先生賜名為“季荷”。我覺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難道我這個人將以荷而傳嗎?
前年和去年,每當夏月塘荷盛開時,我每天至少有幾次徘徊在塘邊,坐在石頭上,靜靜地吸吮荷花和荷葉的清香。“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我確實覺得四周靜得很。我在一片寂靜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綠肥、紅肥。倒影映入水中,風乍起,一片蓮瓣墮入水中,它從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卻是從下邊向上落,最后一接觸到水面,二者合為一,像小船似地漂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詩話上讀到兩句詩:“池花對影落,沙鳥帶聲飛。”作者深惜第二句對仗不工。這也難怪,像“池花對影落”這樣的境界究竟有幾個人能參悟透呢?
晚上,我們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邊石頭上納涼。有一夜,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銀光灑在荷花上。我忽聽卜通一聲。是我的小白波斯貓毛毛撲入水中,它大概是認為水中有白玉盤,想撲上去抓住。它一入水,大概就覺得不對頭,連忙矯捷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離破碎,好久才恢復了原形。
今年夏天,天氣異常悶熱,而荷花則開得特歡。綠蓋擎天,紅花映日,把一個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滿而又滿,幾乎連水面都看不到了。一個喜愛荷花的鄰居,天天興致勃勃地數荷花的朵數。今天告訴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訴我,有六七百朵。但是,我雖然知道他為人細致,卻不相信他真能數出確實的朵數。在荷葉底下,石頭縫里,旮旮旯旯,不知還隱藏著多少??兒,都是在岸邊難以看到的。粗略估計,今年大概開了將近一千朵。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觀了。
連日來,天氣突然變寒。好像是一下子從夏天轉入秋天。池塘里的荷葉雖然仍然是綠油一片,但是看來變成殘荷之日也不會太遠了。再過一兩個月,池水一結冰,連殘荷也將消逝得無影無蹤。那時荷花大概會在冰下冬眠,做著春天的夢。它們的夢一定能夠圓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枸杞樹
在不經意的時候,一轉眼便會有一棵蒼老的枸杞樹的影子飄過。
這使我困惑。
最先是去追憶:什么地方我曾看見這樣一棵蒼老的構記樹呢?是在某處的山里么?是在另一個地方的一個花園里么?但是,都不像。
最后,我想到才到北平時住的那個公寓;于是我想到這棵蒼老的枸杞樹。
我現(xiàn)在還能很清晰地溫習一些事情:我記得初次到北平時,在前門下了火車以后,這古老都市的影子,便像一個秤錘,沉重地壓在我的心上。
我迷憫地上了一輛洋車,跟著木屋似的電車向北跑。
遠處是紅的墻,黃的瓦。
我是初次看到電車的;我想,電不是很危險嗎?后面的電車上的腳鈴響了;我坐的洋車仍然在前面悠然地跑著。
我感到焦急,同時,我的眼仍然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我仍然看到,紅的墑,黃的瓦。
終于,在焦急、又因為初踏入一個新的境地而生的迷惘的心情下,折過了不知多少滿填著黑土的小胡同以后,我被拖到西城的某一個公寓里去了。
我仍然非常迷憫而有點兒近于慌張,眼前的一切都仿佛給一層輕煙籠罩起來似的。
我看不清院子里有什么東西,我甚至也沒有看清我住的小屋。
黑夜跟著來了,我便糊里糊涂地睡下去,做了許許多多離奇古怪的夢。
雖然做了夢,但是卻沒有能睡得很熟。
剛看到窗上有點發(fā)兒白,我就起來了。
因為心比較安定了一點兒,我才開始看得清楚:我住的是北屋,屋前的小院里,有不算小的一缸荷花,四周錯落地擺了幾盆雜花。
我記得很清楚:這些花里面有一棵仙人頭,幾天后,還開了很大的一朵白花,但是最惹我注意的,卻是靠墻長著的一棵構記樹,已經長得高過了屋檐,枝干蒼老鉤曲,像千年的古松,樹皮皺著,色是黝黑的,有幾處已經開了裂。
幼年在故鄉(xiāng)的時候,常聽人說,枸杞樹是長得非常慢的,很難成為一棵樹。
現(xiàn)在居然有這樣一棵虬干的老枸杞樹站在我面前,真像夢;夢又掣開了輕渺的網,我這是站在公寓里么?于是,我問公寓的主人,這構記有多大年齡了,他也渺茫:他初次來這里開公寓時,這樹就是現(xiàn)在這樣,三十年來,沒有多少變動。
這更使我驚奇,我用驚奇的眼光注視著這蒼老的枝干在沉默著,又注視著接連著樹頂的藍藍的長天。
就這樣,我每天看書乏了,就總到這棵樹底下徘徊。
在細弱的枝條上,蜘蛛結了網,間或有一片樹葉兒或蒼蠅蚊子之流的尸體粘在上面。
在有太陽或燈光照上去的時候,這小小的網也會反射出細弱的清光來。
倘若再走近一點兒,你又可以看到許多葉上都爬著長長的綠色的蟲子,在爬過的葉上留了半圓的缺口。
就在這有著缺口的葉片上,你可以看到各樣的斑駁陸離的彩痕。
對了這彩痕,你可以隨便想到什么東西:想到地圖,想到水彩畫,想到被雨水沖過的墻上的殘痕,再玄妙一點兒,想到宇宙,想到有著各種彩色的迷離的夢影。
這許許多多的東西,都在這小的葉片上呈現(xiàn)給你。
當你想到地圖的時候,你可以任意指定一個小的黑點兒,算作你的故鄉(xiāng)。
再大一點兒的黑點兒,算作你曾游過的湖或山,你不是也可以在你心的深處浮起點兒溫熱的感覺么?這蒼老的枸杞樹就是我的宇宙。
不,這葉片就是我的全宇宙。
我替它把長長的綠色的蟲子拿下來,摔在地上。
對著它,我描畫著自己種種涂著彩色的幻象。
我把我的童稚的幻想,拴在這蒼老的枝干上。
在雨天,牛乳色的輕霧給每件東西涂上一層淡影。
這蒼黑的枝干更顯得黑了。
雨住了的時候,有一兩個蝸牛在上面悠然地爬著,散步似的從容。
蜘蛛網上殘留的雨滴,靜靜地發(fā)著光。
一條虹從北屋的脊上伸展出去,像拱橋不知伸到什么地方去了。
這枸杞的頂尖就正頂著這橋的中心。
不知從什么地方來的陰影,漸漸地爬過了西墻。
墻隅的蜘蛛網,樹葉濃密的地方仿佛把這陰影捉住了一把似的,浙漸地黑起來。
只剩了夕陽的余暉返照在這蒼老的枸杞樹的圓圓的頂上,淡紅的一片,焰耀著,儼然如來佛頭頂上金色的圓光。
以后,黃昏來了,一切角隅皆為黃昏所占領了。
我同幾個朋友出去到西單一帶散步。
穿過了花市,晚香玉在薄暗里發(fā)著幽香。
不知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我曾讀過一句詩:黃昏里充滿了木樨花的香。
我覺得很美麗。
雖然我從來沒有聞到過木樨花的香,雖然我明知道現(xiàn)在我聞到的是晚香玉的香。
但是我總覺得我到了那種縹緲的詩意的境界似的。
在淡黃色的燈光下,我們摸索著轉近了幽黑的小胡同,走回了公寓。
這蒼老的枸杞樹只剩下了一團凄迷的影子,靠北墻站著。
跟著來的是個長長的夜。
我坐在窗前讀著預備考試的功課。
大頭尖尾的綠色小蟲,在糊了白紙的玻璃窗外有所尋覓似的撞擊著。
不一會兒,一個從縫里擠進來了,接著又一個,又一個。
成群地圍著燈飛。
當我聽到賣玉米面悸悖戛長的永遠帶點兒寒冷的聲音,從遠處的小巷里越過了墻飄了過來的時候,我便捻熄了燈.睡下去。
于是又開始了同蚊子和臭蟲的爭斗。
在靜靜的長夜里,忽然醒了,殘夢仍然壓在我心頭,倘若我聽到又有?O?@的聲音在這棵蒼老的枸杞樹周圍,我便知道外面又落了雨。
我注視著這神秘的黑暗,我描畫給自己:這枸杞樹的蒼黑的枝干該更黑了罷;那只蝸牛有所趨避該匆匆地在向隱僻處爬去罷;小小的圓的蜘蛛網,該又捉住雨滴了罷;這雨滴在黑夜里能不能靜靜地發(fā)著光呢?我做著天真的童話般的夢。
我夢到了這棵蒼老的枸杞樹--這枸杞樹也做夢么?第二天早晨起來,外面真的還在下著雨。
空氣里充滿了清新的沁人心脾的清香。
荷葉上頂著珠子似的雨滴,蜘蛛網上也頂著,靜靜地發(fā)著光。
在如火如荼的盛夏轉入初秋的澹遠里去的時候,我這種詩意的,又充滿了稚氣的生活,終于不能繼續(xù)下去。
我離開這公寓,離開這蒼老的枸杞樹,移到清華園里來,到現(xiàn)在差不多四年了。
這園子素來是以水木著名的。
春天里,滿園里怒放著紅的花,遠處看,紅紅的一片火焰。
夏天里,垂柳拂著地,濃翠撲上人的眉頭。
紅霞般的爬山虎給冷清的深秋涂上一層凄艷的色彩。
冬天里,白雪又把這園子安排成為一個銀的世界。
在這四季,又都有西山的一層輕渺的紫氣,給這園子添了不少的光輝。
這一切顏色:紅的,翠的,白的,紫的,混合地涂上了我的心,在我心里幻成一副絢爛的彩畫。
我做著紅色的,翠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各樣顏色的夢。
論理說起來,我在西城的公寓做的童話般的夢,早該被擠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我自己也不了解,在不經意的時候,總有一棵蒼老的枸杞樹的影子飄過。
飄過了春天的火焰似的紅花;飄過了夏天的垂柳的濃翠;飄過了紅霞似的爬山虎,一直到現(xiàn)在,是冬天,白雪正把這園子裝成銀的世界。
混合了氤氳的西山的紫氣,靜定在我的心頭。
在一個浮動的幻影里,我仿佛看到:有夕陽的余暉返照在這棵蒼老的構記樹的圓圓的頂上,淡紅的一片,熠耀著,像如來佛頭頂上的金光。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八日雪之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