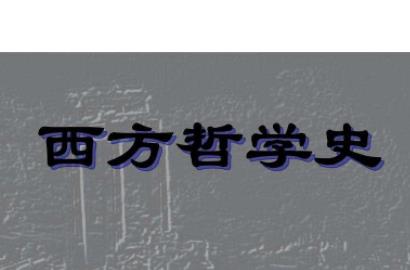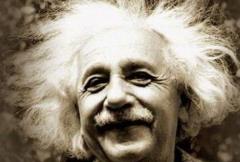�܌W(xu��)����
�܌W(xu��)����(du��)�҂���������ʲô�ã�
2020���¹�����ͻ�����(l��i)����Ğ�(z��i)�y��(d��ng)ǰ������(g��)�Ї�(gu��)���(hu��)ͣ�[�������]�i�ڼ��С���ֹͣ������ζ����Ϣ����ͣ���������錍(sh��)�r(sh��)��(sh��)����Ȼ�˾��ģ�Ó�x��������������(hu��)��˲�g���l(f��)��yҲ���l(f��)˼����
��1978��ĸ��_(k��i)���_(k��i)ʼ������40��������(g��)�Ї�(gu��)�ڸ��ٰl(f��)չ�ı��ߣ�ֱ����?y��n)������ͣ�[���҂����ի@�������f(shu��)�����҂��Gʧ��ʲô��
�҂�ʧȥ�˃ɂ�(g��)����һԻ��η�����һԻ�������ġ�
�˕�(hu��)�ڸ��ٰl(f��)չ�гɞ��ٶȵĹ��߽�(j��ng)��(j��)�İ�������˵ăr(ji��)ֵ�^�ǹ��ߡ�
������r(sh��)�����c��������ɞ鳣�B(t��i)�� �҂�?c��)�Ҳ�o(w��)���ص�����֮ǰ�������B(t��i)�������ؽ��������֮ʧȥ��һЩʲô��
���������ʹ�����(l��i)�����挦(du��)ʹ�࣬�ڽ̺��܌W(xu��)�������Ҫ�ČW(xu��)��(w��n)��������r(sh��)����Ҫ�҂��������������܌W(xu��)�W(xu��)�f(shu��)��(l��i)�^���҂���(gu��)�Һ���������\(y��n)��
��ô��ʲô���܌W(xu��)���܌W(xu��)���T���ӵČW(xu��)��(w��n)��
���������������(g��)ȥ̎���ڽ̡��܌W(xu��)��ˇ�g(sh��)��
�����f(shu��)�܌W(xu��)�](m��i)�ã��܌W(xu��)�Л](m��i)����̎��Ҫ�����^��̎���ǂ�(g��)��(bi��o)��(zh��n)��ʲô��
�����(bi��o)��(zh��n)���f(shu��)�@��һ�T֪�R(sh��)�܉�(l��i)��(sh��)�õăr(ji��)ֵ���܉����҂��Ľ�(j��ng)�(y��n)�����I(l��ng)��(d��ng)���������ơ��҂��Ľ�(j��ng)�(y��n)�����������ƣ���ô�܌W(xu��)�Ĵ_���o(w��)��̎��
����������һ���V�Z(y��)�f(shu��)�����܌W(xu��)�����Á�(l��i)���������
��?y��n)鿾�����Ҫ���Ǿ��w��(j��ng)�(y��n)�ͼ��ɣ��܌W(xu��)�����@�N��(j��ng)�(y��n)�ͼ��ɣ�����ij�N���w��֪�R(sh��)�ͼ��g(sh��)��
�����҂�Ҳ��һ��Ԓ���Իش��@��(g��)�V�Z(y��)���Ǿ��ǣ�
�����ϛ](m��i)��һ�K����Dz���˼����һ��(g��)�܌W(xu��)��(w��n)�}֮��ſ�����(l��i)�ġ�
ʲô�܌W(xu��)��(w��n)�}�أ�
������To be or not to be����
����ķ���ء��ǂ�(g��)�������_(t��i)�~����������߀���������@��һ��(g��)��(w��n)�}����
�҂��Ԟ��҂������]���҂��䌍(sh��)ÿ�춼�ڻش��@��(g��)��(w��n)�}���������ѽ�(j��ng)�Q���ˡ�not to be���ˣ���߀��ʲô����أ�
���c��(d��ng)��ą^(q��)�e�����ڴˣ���(d��ng)��������H�H�ǻ���������H��������֪���Լ�������
�@�N֪����һ�N���\(y��n)Ҳ�Dz��ҵ��_(k��i)ʼ����?y��n)��҂�����һ���?z��)�Σ�ȥ���Z�������@�N���Z��Ҫ���x���A(ch��)����Ȼ�y�ԾSϵ��
�����x���A(ch��)���Ǒ{�ն���(l��i)�����ĿȾ��ѭ���У�����������Ļ����y(t��ng)�c�Ļ������Ё�(l��i)��
�܌W(xu��)�Ξ�
���fƬ��(zh��n)��(zh��ng)���_(k��i)��(gu��)�T�_(k��i)ʼ���Ї�(gu��)�˾�չ�_(k��i)�ˌ�(du��)��(gu��)�����c�ƶȵ�˼�档�����f(shu��)��(gu��)�����е�ū�����ƶȵ��������f(shu��)�ƶȵ����Դ�ԇ�(gu��)���Եĉ��䡣�������ƶȸ����Ǹ�����߀�LJ�(gu��)���Ը����Ǹ������ƶ��c��(gu��)���ԃ��ߵ����l(shu��)�Q���l(shu��)��
���S���ƶ����(f��)һ���Տ�(f��)һ�յ���ǰ���䣬�ʬF(xi��n)ε����^�ĸ��ƣ���(gu��)����ǧ������ʣ���ƿ�b�¾�߀����ƿ�b�f���ƺ���Ȼ�o(w��)���q�ס�
�܌W(xu��)�ڱ��Ƶ����Ǻ������µĻش�
�ڸ�һ���܌W(xu��)��(sh��)������С߉�������@��һ��Ԓ���������҂���(du��)�ɂ�(g��)�����P(gu��n)ϵ�����⣬�_(d��)����������õ������Ԓ����ô�҂�����߀�](m��i)���M(j��n)������ֻ��վ�ڸ�����T���ϡ���
�ƶȺ͇�(gu��)���Ծ�����ʲô�P(gu��n)ϵ������á�
�_(d��)��������õ�����߀�](m��i)�M(j��n)������߀վ�ڸ�����T���ϡ�
��ô������ʲô��
�������҂�?n��i)�����˹���_(d��)�˵��L(f��ng)���ƶȺ�˹���_(d��)�˵��Ը����֮�g�P(gu��n)ϵ��Ԓ��
�҂�һ��������f(shu��)��˹���_(d��)��֮��������@����Ը���?y��n)��������L(f��ng)���ƶ����;���҂�Ҳ���Ե��^(gu��)��(l��i)�f(shu��)��˹���_(d��)��֮��������@����L(f��ng)���ƶ���?y��n)��������Ը���ˡ?/p>
�����҂�ֻ���@�ӵ����⣬�҂���(hu��)�l(f��)�F(xi��n)�@��������Q���ģ������䌍(sh��)�҂�?c��)��@�N�����ϣ��҂��ț](m��i)������˹���_(d��)�˵��Ը�Ҳ�](m��i)����������˹���_(d��)�˵��L(f��ng)���ƶȣ���?y��n)��@�ɘ�?x��n)|������(l��i)��һ��(g��)��ͬ�ġ��������ģ��Ǿ���˹���_(d��)������������Ҫ�ø���ȥ���յġ���
�Ї�(gu��)�ġ����ס����f(shu��)�����ζ������^֮�����ζ������^֮������
���@��(g��)���ֻ�DZ���֮�����߀����ָ����ĵ����ƶȡ�
��ô���ζ����ߡ����Dz��ɱ�ֱ�ӽ�(j��ng)�(y��n)��������֪���ģ����ǵ���
���ԟo(w��)Փ���ƶ�߀�LJ�(gu��)���Ը�ʼ�Kͣ�������Č��档�����ƶ���������(gu��)���Ը�Ҳ������
����ź͵����P(gu��n)��˹���_(d��)���Ļ�������˹���_(d��)�ˌ�(du��)�����I(l��ng)��(hu��)�������҂��о��Ї�(gu��)�Ć�(w��n)�}���о��Ї�(gu��)���ƶȣ��о��Ї�(gu��)�˵��Ը��҂���KҪ�о����Ї�(gu��)�ˌ�(du��)�����I(l��ng)��(hu��)��
�܌W(xu��)���ǿƌW(xu��)�����ǽ�(j��ng)�(y��n)��߉�Ŀ��ɣ��܌W(xu��)����Փ���ČW(xu��)��(w��n)���܌W(xu��)��Փ���ČW(xu��)��(w��n)��
����һ�е������o(w��)Փ�����|(zh��)����߀�Ǿ������������(l��i)�����Č�(du��)�����I(l��ng)��(hu��)�������|(zh��)����ȡ�Q���ˌ�(du��)���c��Ȼ���P(gu��n)ϵ���I(l��ng)��(hu��)���������ȡ�Q���ˌ�(du��)���c���P(gu��n)ϵ�����(hu��)�����I(l��ng)��(hu��)��
����֮��
�������嶼��Փ���ģ��W���ˏĹ�ϣ�D�_(k��i)ʼՓ�����Ї�(gu��)�ˏ����صĕr(sh��)���_(k��i)ʼՓ�������Ў�ǧ��Ěvʷ��
Ҋ(ji��n)��ʧ��Ҫ����(w��n)�}����?y��n)�?du��)�������a(b��)ʼ�K���ڱ��棬���Ԯ�(d��ng)���Ї�(gu��)Ҫ����Փ����������Փ���͕�(hu��)���R�������܌W(xu��)�IJ�c�_ͻ����(d��ng)�����c����o(w��)���x��ĕr(sh��)�͕�(hu��)��׃?y��u)����(g��)�����I(l��ng)����������r(ji��)ֵ�^�ě_ͻ��������ͥ���
���������Փ����
��Մ��ϣ�D��Մ���������Y�����x���������İl(f��)չ��һ��(g��)��Ҫ���Ļ�����ǰ�ᡪ��˽��ؔ(c��i)�a(ch��n)�c�˸�ֱ��(li��n)ϵ��
���w��(hu��)���w���磬���˸�Խ�r(sh��)�g���ޣ������������˵�˽��ؔ(c��i)�a(ch��n)��(sh��)�|(zh��)�������˸���x��
�����܌W(xu��)ӑՓ�ľ����@�N���(hu��)����ɞ���ܵĻ��A(ch��)���@����Փ�������(hu��)����ĸ���(j��)�ǵ���Դ���@��(g��)����(j��)��(l��i)�������ƶȵȵȣ���������
�����������@��(g��)������ԅ^(q��)�֞�ɂ�(g��)���磬һ��(g��)�ǿ���ֱ�Ӹ�֪���ĸ������磬߀��һ��(g��)�����dz����X(ju��)�ģ��ÿ��µ�Ԓ�б��w�����˼�硣
�Ї�(gu��)�����Փ����
�Կ��Ӟ��������������ġ��ʡ�������ij�N���Եij���������һ�N������С�
��Փ�Z(y��)����ӛ�d�����ӵČW(xu��)�����膖(w��n)���ӣ�����ĸ������Ů��Т�����Ƿ�̫�á������ӛ](m��i)������ش𣬶��Ƿ���(w��n)���裺���������Т�������\�C��ʳ�����磬���İ���������Ի���������������ߺ��ӸЇ@������֮����Ҳ����
���膖(w��n):������֮��,���Ѿ��ӡ��������겻��Y,�Y�؉ġ����겻�阷(l��),��(l��)�ر�������Ի:��ʳ��,�·��\,��Ů(��)��?��Ի:����������Ի:����֮����Ҳ��
ʲô���ʣ�ȡ�Q�ڡ��İ��c������ij��(g��)�����������������Тԓ��ã�
��ô���^���İ��c������һ�N������С�
�K���������ǷN���������ߵĸ������������ӵ��ʸ�������������������С�
�Ї�(gu��)�܌W(xu��)����ʾ���������������������е����࣬Ó�x������е�����ֻ�dz��������Ҏ(gu��)�t��
�����˵������������Ќ��ң��Ї�(gu��)�˵������������У�Ҳ���^(q��)�ָ��Ժ����ԣ�����ֱ���ڸ������ҡ�
�����������Ќ��ң���������Ю�(d��ng)���U�l(f��)���@�����Ї�(gu��)�܌W(xu��)��·��(sh��)��